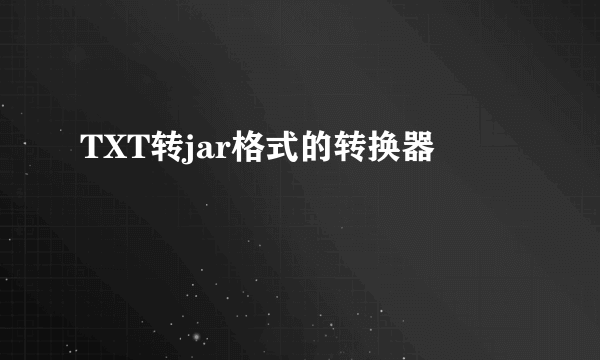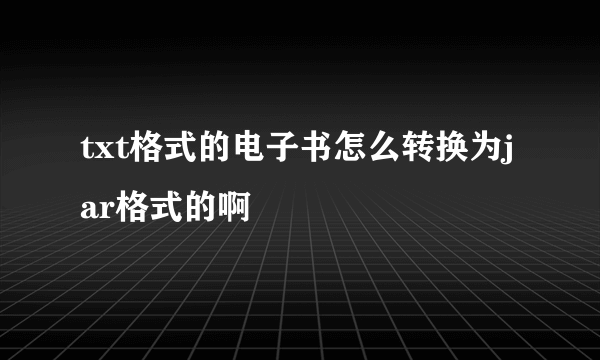求倪萍的《姥姥语录》TXT版本全集有的发达812898369@q,谢谢
的有关信息介绍如下: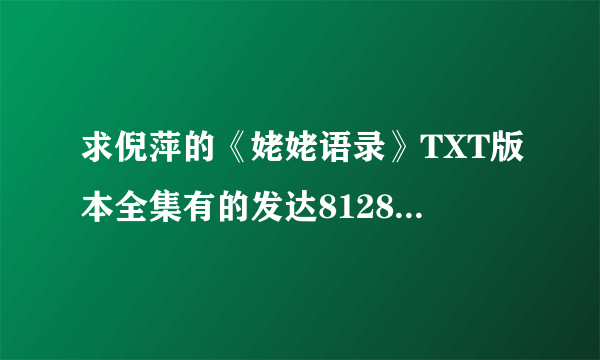
姥姥语录
作者: 倪萍 发表时间: 2012-1-19 7:53:00 所属类型:现代文学
正文
目录 开篇 心到就好 天黑了(1)
天黑了(2) 天黑了(3) 我不敢为她送行
姥姥挣钱了(1) 姥姥挣钱了(2) 姥姥挣钱了(3)
姥姥挣钱了(4) 姥姥挣钱了(5) 好心加好心,就是搅人心(1)
好心加好心,就是搅人心(2) 姥姥的冬天(1) 姥姥的冬天(2)
三个爸爸(1) 三个爸爸(2)
正文
目录
( 本章字数:1227 更新时间:2012-1-19 7:53:00 )
开篇心到就好
Ⅰ.遗憾就是专门留下的……
天黑了
我不敢为她送行
姥姥挣钱了
三个爸爸
骨肉相连,分开了就出血
如果有下辈子……
Ⅱ.人生或许就该是这样……
什么日子都是掺合着过
两个妈
爱不怕分,越分越多
自己不倒,啥都能过去
姥姥的金元宝
Ⅲ.快乐你别嫌它小……
小幸福一天一个
倒过来想,换个个儿看
一句话的力量
给予是幸福,欠人家是受罪
Ⅳ.智慧如同储蓄卡……
姥姥和季羡林是同学
写书也不是多大的事
我的老师是姥姥
人生就要上山顶
眼要是吃不饱,人就像个傻子
刷不爆的银行卡
一个孩子穿十件棉袄,那不烧坏了
(附:水门口比北京好)
结束语天籁之声
附录:姥姥最受用的智慧语录
[ 置 顶 返回目录 ]
开篇 心到就好
( 本章字数:2920 更新时间:2012-1-19 7:53:00 )
写本《姥姥语录》是姥姥生前我俩就说定了的。
记得第一次跟姥姥说这事的时候,她那个只剩下一颗牙的嘴笑得都流出了哈喇子:“人家毛主席说的话才能叫语录,我一个大字不识的老婆子说的些没用的话还敢叫语录,那不叫人笑掉大牙?”
躺在姥姥的床上的我也笑翻了。你想嘛,一个只剩下一颗牙的人还说“笑掉大牙”,多可笑呀。
我跟姥姥商量:“是现在写,还是……”
姥姥接话可快了:“等我死了再写吧,反正丢人我也不知道了。光着腚推磨,转着圈丢人,你自己丢去吧,反正你脸皮也厚。”
“你可别后悔呀老太太,你是作者之一,咱俩联合出版。刘鸿卿、倪萍,我把你大名写在前头,稿费咱俩各一半儿。”
姥姥眼睛一亮。
想起十四年前写《日子》那会儿,姥姥陪在我身边,我坐着写,她站着翻,我写一张她翻一页,可怜的姥姥翻半天也不知道我都写了些啥,偶尔给她念一段,她还常常制止:“别为我耽误那些工夫了。起早贪黑地写能挣多少钱?”
“一本书二十二块。”
“那还真不上算,写这么些个字才二十二块,连个工夫钱都挣不回。不上算,不上算??”
呜,姥姥以为我一共才挣二十二块呢!
只剩一颗牙的姥姥忧伤地望着窗外:“咳,俺这阵儿要钱可是一点用也没有了。天黑了,俺得走喽,俺那个地方一分钱也不用花……”姥姥知道自己要走了。
前年,活了九十九岁的姥姥真的走了,我的天也黑了。
姥姥是我家的一杆秤,遇到啥事上姥姥的秤上称一称,半斤八两所差无几。
姥姥走了,留下了秤。
姥姥的秤有两杆,大秤、小秤。她的大秤是人人都可以称的,叫公家的秤,是以大多数人的利益和公平为准星的,小秤是自家的秤。大秤、小秤的秤砣分量相差很大。
我也曾让她称过《姥姥语录》,姥姥说:“上大秤称也就二两吧,咱家的秤能称个十两八两的。”
在姥姥的眼里,家里多大的事上了公家的秤都是很轻的分量。姥姥说得真准,现如今图书市场那么繁荣,好书有的是,一本小画书真的也就二两吧。但我还是拿起笔写了,因为姥姥语录得张贴出去。
姥姥的语录当真那么需要让外人看看吗?列出三十个题目后我也茫然了。真像姥姥说的那样,字里字外都是些“人人都明白的理儿,家家都遇上过的事儿”,有必要再唠叨吗?
稿纸放在桌子上,每天该忙啥忙啥。怪了,常常是忙完了该忙的事就身不由己坐到桌前往稿纸上写字。几天下来,满纸写的都是姥姥的语录。
这些萝卜白菜的理儿,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我怎么那么念念不忘呀?是我老了吧?是我跟不上这个时代了吧?可是认识姥姥的人,熟悉我的朋友见了我总是问起姥姥,提起姥姥语录。
敬一丹每回见了我一定有一句话是不忘的:“姥姥还好吧?”只是一年比一年问的语气迟缓。
去年主持人“六十年六十人”在浙江颁奖,她又问:“姥姥……还……好吗?”我说:“不好,走了。”一丹说她始终不敢问,是因为姥姥快一百岁了,问候都得小心翼翼。
中午吃饭,张越、岩松、一丹我们坐一桌,又说起了姥姥,说得一丹大眼睛哗哗地流泪,其实我们说的也都是些白菜萝卜的事。张越说“三八”百年庆典,她就想请姥姥这样一位普通百姓做嘉宾,我心想,如果姥姥在,她那些小得不能再小的事拿到全国观众面前,不就真成了姥姥说的让观众“笑掉大牙”了吗?姥姥说:“人最值钱的就是知道自己几斤几两,没个分量你往大秤上站站试试?那个秤砣动都不动。”
白岩松也是。去年我和他去上海参加《南方周末》二十五周年庆,回来的飞机上我们又说起姥姥。一路的飞行,一路的姥姥。飞机落地了,姥姥还在我俩的嘴边挂着。
岩松说:“有学历的人,不一定有文化;没学历的人,不一定没文化。”临说再见,他还嘱咐我:“倪姐,快写写姥姥吧,我们需要姥姥的精神。”
我咬着牙不写姥姥。
《南方周末》希望我开个专栏专门写姥姥,为此他们的副主编和张英还专程来北京找我说这个事儿,我也始终没有动笔。这些年本子上胡写乱划了很多字,但很少写姥姥—近乡情怯?不知道。这是我最爱的人,是我最了解的人,也是离我最近的人,可是落在纸上却常常模糊不清,好像我就是她,她就是我。
随着姥姥的远去,我充盈的泪水逐渐往心里流淌的时候,想念灌满了我的灵魂,我开始寻找姥姥。家里每一个角落、每一样东西都是我们和姥姥一同拥有的,现在这个人不在了,我找不到了。
可是冥冥之中,姥姥又无处不在。
我知道,我是一直不敢找!我知道,还用找吗?姥姥一直都在我心里,在我的灵魂里。不用想念,姥姥没死,走了的只是那个躯体。
我开始和姥姥说话了。
儿子说:“妈妈,这几天你老说山东话。”
“是吗?”
我知道,不是我在说,是姥姥在说。
[ 置 顶 返回目录 ]
天黑了(1)
( 本章字数:2010 更新时间:2012-1-19 7:53:00 )
姥姥说:“天黑了,谁能拉着太阳不让它下山?你就得躺下。孩子,不怕,多黑的天到头了也得亮。”
姥姥走的那年春节我还跟她说:“挺住啊老太太,使使劲,怎么着咱们也得混个百岁老人。”
姥姥说:“有些事能使使劲,有些事啊就使不上劲了,天黑了,谁也挡不住喽!”
“姥姥,你怕死吗?”
“是个人就没有不怕死的。”
“那你这一辈子说了多少回‘死了算了’?好像你不怕死,早就活够本儿了。”
“孩子你记住,人说话,一半儿是用嘴说,一半儿是用心说。用嘴说的话你倒着听就行了,用心说的话才是真的。”
“哈哈,老太太,那你这一辈子说了半辈子假话呀?”
“也不能这么说。你想啊,说话是不是给别人听的?哪有自己对自己说的?给别人听的话就得先替别人想,人家愿不愿意听,听了难不难受、高不高兴。这一来二去,你的话就变了一半儿了。你看见人家脸上有个黑点,你不用直说。人家自己的脸,不比你更清楚吗?打人不打脸,揭人不揭短。你要真想说,你就先说自己脸上也有个黑点,人家听了心里就好受些了。”
哦,凡事要替别人想。
“姥姥,你走了以后我想你怎么办?每年清明还得给你上坟吧?”
“不用,活着那些人就够你忙乎的了,人死了啥都没有了,别弄这些个没有用的摆设了,那都是弄给别人看的。我认识你这个人快五十年了,我最知道你了,不用上坟。”
姥姥走后我真的没敢去看她。
越不敢去心里越惦记。
去年夏天,儿子去姥姥家的水门口村过暑假,我派他代我去看看老奶奶。儿子回来说,老奶奶就躺在村口河边一个小山包的一堆土里。土堆前有块石头,上面写着姥爷和姥姥的名字:倪润太、刘鸿卿,土堆上面有些绿草,别的啥都没有了。儿子用手比划着土堆的大小,看着他那副天真的样儿,我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怎么也挡不住。很久没有这样哭了,心疼姥姥如今的日子,孤单、清冷。
我也最知道姥姥了,她本质上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一副柔弱的肩膀,一双三寸的小脚,热热闹闹忙忙乎乎地拉扯了一大群孩子以及孩子的孩子,走的时候是四世同堂。
这是姥姥想要的日子吗?是,其实也不是。
“姥姥,如果还有来世,你还会生那么多孩子吗?”
姥姥反问我:“你说呢?”
我不希望姥姥再那么辛苦了,“不生了”。
我也不生。如果还是做主持人、做演员这个工作,我就不要孩子也不要家。我盼着现场直播之前,先在一个安静的属于自己的花园房子里睡上一大觉,起来洗个澡、喝一杯咖啡,再清清爽爽地去化妆,精精神神地去演播厅,无牵无挂。晚上回来,舒舒服服地泡上一个玫瑰浴,点一支香烟,喝一杯红酒,翻一本闲书。哪像现在呀,给全家蒸上包子,熬上稀饭,抹把脸就提溜着裙子去直播了。不管多晚回家,一大家子人还等着你,温暖是温暖了,可累人、累心啊!我都佩服自己,那些年是怎么混下来的?
“人哪,就是穿着棉袄盼着裙子,穿着裙子又想着棉袄。要不是这些人在家等着你,你在电视上兴许就不会说人话了。”
明白姥姥的意思了吧?这是对我主持风格的高度评价:说人话。
“那你的意思,来世你还会选择当一个这么多孩子的母亲,当一个这么多孙子、外甥(山东等地称外孙、外孙女为外甥)的奶奶、姥姥?”
[ 置 顶 返回目录 ]
天黑了(2)
( 本章字数:1929 更新时间:2012-1-19 7:53:00 )
“你和我不一样,你生下来是为老(好)些人活着的,有杆大秤称着你,俺这路人都是小秤盘里的人,少一个多俩的都一样。”
姥姥始终没给个具体答案。她不能想象没有家人、没有孩子,她这一生怎么个过法,但是姥姥觉得我是可以一个人成为一个家的那种人,我是有社会使命的那个人。哈,真会戴高帽子,谁给我的使命?
“姥姥,有多少家人、有多少孩子,最后走时还不是孤身一人?谁能携家带口地走啊?”
姥姥笑了:“分批分个儿地走啊,就像分批分个儿地来一样,早早晚晚地又走到一块儿了。”
是安慰还是信念?姥姥始终相信下辈子我们还是一家人。这是她对家的无限眷恋和对生命延续的阐释。
人为什么终究是会死去的呢?
知道姥姥走了的那天我在东北拍戏。晚上六点刚过,哈尔滨已经天黑了,小姨发来一条短信:“六点十分,姥姥平静地走了。”看了短信,我竟然很平静,无数次地想过姥姥的走,天最终是要黑的。我一滴眼泪也没掉,只是不停地在纸上写着“刘鸿卿”三个字,姥姥的名字。
一个不认字的老太太还有个挺有学问的名儿!她的父亲是个识文断字的人。只因为姥姥生为女性,否则她一定是个“念大本书、写大本字的读书人”。这是姥姥对文化人的评述,也是她常指给我们晚辈儿的光明之道。
天黑了,姥姥走了,窗外冒青烟的雪无声地陪着我。屋里漆黑一片,我庆幸这样的时刻身边没别人,这是我最向往的时刻,我的心是自由的。我把写满姥姥名字的纸贴在结了冰又有哈气的双层玻璃窗上,“刘鸿卿”三个字化开了,模糊了,看不清了,升腾了……
看着小姨的短信,心里想的却是半个月前和姥姥在威海见的最后一面。我这位认识了快五十年的最亲的人、最爱的人、最可信赖的老朋友一句话也没和我说,我甚至觉得她都不知道我在她身边。我们就这样永久地分开了,从此天上人间。
其实,姥姥病危的通知已经发了三次了,我心里早有准备,这个早恨不能童年就有。
太爱一个人、太依赖一个人,就一定最怕这个人离你而去。小时候惹大祸了,姥姥最重的一句话就是:“小外甥啊,你得气死我呀!”多大的错我一下子就能改了。
“没有了姥姥我怎么办?”
“有你妈呀!”
那时我觉得姥姥就是妈,妈就是姥姥。
我经常问:“为什么不是先有姥姥后有妈呀?”
姥姥也不避讳生孩子、结婚这类小孩子不能听的“秘密”,所以三岁多的我就敢在众人饭桌上大声地说:“我知道我姥姥和姥爷睡了觉,嘀里嘟噜地生了我妈、我大舅、我大姨……我妈我爸又嘀里嘟噜地生了我和我哥,我又嘀里嘟噜地生了我的孩子……”
众人大笑。我妈嫌姥姥太惯我,教育方法太农民,姥姥却欢喜:“一堆孩子都这么拉扯大的,同样的饭,同样的话,萍儿这孩子就是块有数的海绵,该吸收的一点也拉不下。”
偶尔发个烧,即使烧得很高,姥姥也从不带我去医院。她像揉面一样把我放在炕上,浑身上下从头到脚揉上一遍,揉过的我就像被水洗过一样,高烧立刻就退了。再看看姥姥,出的汗比我还多。享受着姥姥的敲打,体味着姥姥的汗水,高烧一次,长大一次。那时我盼着姥姥也高烧,我也想用汗水洗一遍衣服,可姥姥从来不病。
长大了才知道,姥姥的病是到九十九要死了才叫病啊!一生都不给别人添麻烦的人病了也不是病啊,想想这些我的心生疼,连生病都不舍得,铁打的姥姥啊!
[ 置 顶 返回目录 ]
天黑了(3)
( 本章字数:3183 更新时间:2012-1-19 7:53:00 )
五十年了,活在我面前的姥姥从来都是一副硬硬朗朗的模样,连体重一生也只在上下两斤浮动。健健康康的姥姥,血流充盈的姥姥,怎么会停止呼吸呢?我不敢面对将要死去的姥姥,不敢看只剩下最后一口气的姥姥是什么样子。
我预感,如果再不敢去恐怕就没有机会了。
那天我没跟任何人打招呼,早起七点的飞机就去了威海。出了烟台机场,我打了一辆出租车,三百二十块钱把我送到了威海最好的医院。
五十年了,这是我和姥姥第一次在医院见面。无论是她,无论是我,我们都是多么健康、多么坚强啊。两个一辈子都怕麻烦别人的女人大病没得过,小病没看过,挺挺、咬咬牙就过去了,这最后一面竟然是在医院里。
高级的病床上躺着插满了各种管子的姥姥,一辈子爱美、爱干净、爱脸面的姥姥赤身裸体地被医生护士翻动着。
我跟着姥姥五十年,没给她洗过一次澡,没给她剪过一次趾甲。太好强的姥姥,九十七岁还坚持自己洗澡。浴室的门一定要关上,家里人只能从门缝里“照料”着她,“搀扶”着她。
一个一辈子怕麻烦别人的人在最后的日子里尽情地麻烦着别人,三个姨一个舅妈日夜在病房里守护着姥姥。到了医院,看见姥姥的第一眼我就知道,无论谁在,无论用什么最现代的医疗手段,姥姥的魂儿已经走了,眼前发生的一切都和她无关了。
天黑了。
医生商量要不要上呼吸机,感冒引起的肺部积水致使呼吸困难。
我问上了呼吸机还能活多久,医生很坦率地说:“不好说,毕竟这么大岁数了,身体各个器官都衰竭了。”
“不上了吧。”
切开喉管就得一直张着嘴,用仪器和生命对抗,直到拼完最后一点力气。姥姥还有力气吗?救姥姥还是安抚我们这些她的亲人?我瞬间就把自己放在了姥姥的秤上。
五十年了,我和姥姥无数次地说起过死,挺不住了就倒下吧。
姥姥,你不是说过吗?“天黑了,谁能拉着太阳不让它下山?你就得躺下。孩子,不怕,多黑的天到头了也得亮。”
姥姥的天啥时候亮?这一次会永远地黑下去吗?
那天从进病房一直到离开,八个小时,我一分钟也没坐下,就那么一直站着。是想替姥姥挺着,还是怕自己的心灵倒下?姨们无数次地搬凳子喊“坐下”,我的眼睛始终没离开姥姥,我盼着她睁开眼睛:“孩子,姥姥死不了。”
姥姥,你不是说过吗?“盼着盼着就有望了,盼望嘛。”
我带着盼望离开了病房,电梯门一关我竟失声痛哭,我心里绝望了。姥姥,盼望被绝望压倒了。
八个小时后我又花了三百多块钱回到了烟台机场,当天飞回剧组。第二天拍戏,导演从监视器里看了画面,建议我休息一天,红肿的眼睛里没有了魂儿。
魂儿丢了。
怪不怪,从病房到机场,一路大雨。从小到大,无数次走过这条路,如今竟看不清这条路是去哪儿。和姥姥见的最后一面像是一场梦。
其实五年前姥姥就病危过一次。
粉白色的棉绒寿衣她自己早就备好了,几次嘱咐我们拿出来放在床头上。
“哪天睡着了不再醒了就赶紧给我穿上,省得硬了穿不上。”
我笑她好像死过一样,“你怎么知道是硬的”?
“俺妈就是坐着坐着睡过去的,等中午叫她吃饭时,啊,人都硬了,最后连件衣服都套不上。”
姥姥后悔了一辈子,老母亲临走穿的那件粉白的衣服就定格成了女人最漂亮的寿衣。
要走了的姥姥不吃不喝,我日夜焦虑。什么办法都用了,姥姥依然是半碗汤端上去,汤半碗端下来。
姥姥说:“这几天天天梦见你小舅(小舅四十多年前因公牺牲),你小舅拖我走啊。”
姥姥这句话启发了我,“姥姥,我认识东北的一个神人,这个大姐前些年出了一次车祸,起死回生后成了一个无所不能的神医。我打电话问问她你还能活多久”。
姥姥几天不睁的眼睛突然睁开了,嘴上却说:“哪有神哪,神就是人,人就是神。”
我相信姥姥这回死不了,头脑还这么清醒。于是我赶紧当着姥姥的面儿,给这位“神人”拨通了电话。
“神人”是我表妹,就在隔壁屋等我的“长途”。
“什么?你说得准吗?五年?还能活五年?算今年吗?属狗子的。早上还是晚上生的,你问她自己吧。”我把电话递给了姥姥。
“神人”在电话里问了姥姥的出生时辰和方位。
姥姥的耳朵有些聋,根本听不出是变了音儿的孙女扮演的神人——哈,演出成功。
放下电话,姥姥说了句:“熬碗小米儿喝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