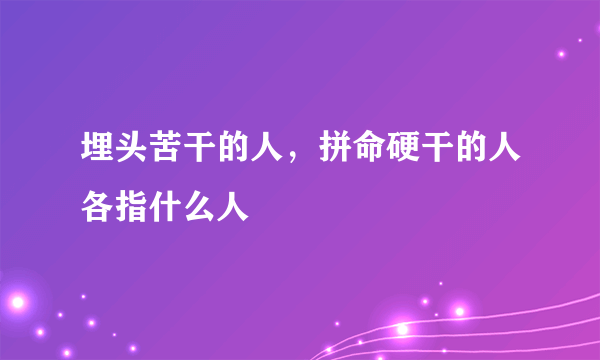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请再举出两种人。
的有关信息介绍如下: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逐渐沦为帝国主义列强的半殖民地。在帝国主义面前,“可怜的民族,奴隶的民族,上上下下都是奴隶。”在某种意义上,整个旧中国就是一个奴隶王国,在这个铁一般黑暗的国度里,帝国主义的奴役与中国古老的封建传统相结合,使中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力受到了极大的摧残,在一部分人当中,甚至丧失殆尽。鲁迅对此痛心疾首,与这种奴隶的“劣根性”进行了坚忍不拔的斗争,但这并不意味着鲁迅认为四万万同胞都已经消极、沉沦乃至堕落,他清醒地看到了问题的另外一面,即中国现实和历史上的“脊梁”。《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就是中华民族脊梁的一曲颂歌。《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写于1934年9月25日,时值“九一八”事变和“七七”事变之间。当时,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在践踏了东北三省之后,又向关内步步进逼,亡国灭种的威胁迫在眉睫,悲观失望的情绪主宰了一部分人的头脑。1934年8月27日《大公报》社评《孔子诞辰纪念》哀叹:“民族的自尊心与自信力,既已荡焉无存,不待外侮之来,国家固早已濒于精神幻灭之域。”针对这种论调,鲁迅在他53岁诞辰时,写下了这篇著名的杂文。作者冷峻的目光首先注视着现实。文章一开头就列举了三种事实:自夸“地大物博”,寄希望于“国联”;“一味求神拜佛,怀古伤今”。这些事实都见之于“公开的文字”,表示言之有据,事实确凿,然后很自然地引出本文批驳的论点:“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但作者当即指出,这个提法本身就是不确切的,因为信“地”,信“物”,信“国联”,这明明是“他信力”,而不是“自信力”。这种以论敌的论据为论据来反驳论敌的论点的方法,使文章在从容不迫的气度中,蕴含着一种无可辩驳的力量。文章在指出一部分人连他信力都已丧失之后,笔锋一转:“失掉了他信力,就会疑,一个转身,也许能够只相信自己,倒是一条新生路。”作者在这里开出的“新生路”,意在反衬下文的“死路”:“玄虚之至”的求神拜佛,只能说明“中国人现在是在发展着‘自欺力’。”这一结论是前文的自然引申,但文笔一波三折,跌宕起伏,在层层递进的推理之中,始终贯穿着逻辑的力量。在批驳了论敌的论点之后,作者深沉的目光由近及远地转向了我们民族古老的历史。他那纵贯古今的思绪首先从严峻的现实中生发开来,指出“自欺”并非现在的新东西,而是古已有之,于今为烈,以致“笼罩了一切”。“笼罩”一词,在这里用得十分准确、形象,它生动地描绘了这种思潮像毒雾一样禁锢着人们的头脑,并蔓延到了各个领域。然后,作者用“然而”一转,满腔热情地歌颂了“在这笼罩之下,我们有并不失掉自信力的中国人在。”他们当中,既包括历史上那些“埋头苦干的人”,“拼命硬干的人”,“为民请命的人”,“舍身求法的人”,更包括现在那些“有确信,不自欺”,“前仆后继的战斗”而又“被摧残,被抹杀”的人。这样,作者的思绪就在追溯历史长河的源流之后,又回到了现实,明确指出:“说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用以指一部分人则可,倘若加于全体,那简直是诬蔑。”文章的结尾提出了判断自信力有无的正确标准:“状元宰相的文章是不足为据的,要自己去看地底下。”“状元宰相”,当是泛指古今封建统治阶级在思想文化战线上的代言人。“地底下”,则是泛指古今一切有自信力的中国人,并与前文的“笼罩”成为鲜明的对照。这样的结尾,既总结了全文,又恰与文章开头“公开的文字”相呼应,使文章结构完整,浑然一体。综观全文,文章以现实为纬,以历史为经组织材料,开头始于现实,然后引申到历史,再由历史回到现实,结尾则既是对历史的总结,又是对现实的概括。文章先破后立,破得有力,立得牢固,驳论与立论相结合,互相映衬。驳论以事实为依据,内含逻辑推理,极其雄辩;立论则直抒胸臆,充满激情;排比句式的运用,更使文章增添了气势;议论与抒情水乳交融,增强了文章的说服力和感染力。《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的核心是论述中国人自信力的有无,因此,正确地理解作者所称颂的有自信力的人的含义,就成了理解这篇杂文的关键。笔者认为,“中国的脊梁”是一个民族的概念,而不仅仅是中华民族中某一阶级、某一集团的概念,在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情况下,更是如此。我们中华民族是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伟大民族,她孕育了千千万万个英雄豪杰,其中既包括劳动人民中的优秀人物,也包括剥削阶级中的志士仁人以及历代统治阶级中的杰出人物。由于历史条件的原因,后者的聪明才智比前者有更多的机会得到发挥;他们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学、艺术等领域为中华民族的发展所做出的贡献,也比后者有更多的可能在史书上有所记载。文中所论及的“埋头苦干的人”,指那些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执着于某一项事业,不畏艰险,奋斗不息的人。就在写作本文之后一年,作者写了历史小说《理水》,塑造了古代治水英雄大禹的形象,可互相印证。“拼命硬干的人”,当指那些置身家性命于不顾,揭竿而起、斩木为兵的农民领袖和精忠报国、壮怀激烈的民族英雄。“为民请命”的确切含义,指的是为老百姓请求保全生命或解除疾苦,这一词语的出处,见《汉书·蒯通传》:“西乡(向)为百姓请命。”“为民请命”这一提法在极“左”思潮泛滥时曾经受到过大规模的口诛笔伐,以至一些教科书的编者在选用这篇杂文时,不得不将这句话从文章中删除。但是,正如一位戏剧家借助剧中人物之口所说的那样:“为民请命,何罪之有?”几乎在写作本文的同时,作者写了历史小说《非攻》,塑造了一个古代为民请命的墨子形象,也可互为印证。“舍身求法”的“法”,这里可做标准,规范解。又,“法”在世界各国语源上都兼有“公平”“正直”“正义”等含义,所以,“舍身求法”可以解做:为追求某一种规范(诸如公平、正义等),不惜牺牲性命,类似“舍生取义”,而“舍生取义”语出《孟子·告子上》,它在本质上属于儒家思想。历代统治阶级中的不少杰出人物,都把它奉为行动的准则,这样的例证,史不绝书。甚至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些先驱,有时也借用这一成语来激励自己的革命意志。可见,作者在这里列举的几种类型的人,都不仅仅限于某一阶级或集团,而是指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精华。鲁迅是实事求是的典范。对于那些所谓“正史”,他虽然借用梁启超的说法,认为它们不过是为帝王将相作家谱,但这并不意味着对历代统治阶级采取简单否定、一笔抹杀的态度,更不意味着对他们中的杰出人物所做的贡献也采取不承认主义。他曾经把汉唐统治者魄力的“雄大”与“闳放”和“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一起来加以肯定;他还推崇被人误认为奸臣的曹操是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至于他称赞一些在文学史上做出重要贡献的诗人和散文家的例子,就更是俯拾皆是了。对于那些被现代的某些人改铸得无比高大的农民起义领袖,鲁迅也从未做过无原则的歌颂,而是毫不掩饰他们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他对明末农民起义领袖张献忠多有针砭,即是一例。同样,现实生活里的“脊梁”,既包括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革命人民,也包括中华民族中其他阶级和集团中的杰出人物。就在作者写作本文之前两年,在日本帝国主义挑起的“一二八”事变中,驻守上海的十九路军就曾奋起抵抗,重创敌人,使之四易司令。在作者写作本文之前一年,二十九军又血战喜峰口,以大刀和血肉之躯与敌人拼搏,震惊中外。国民党军队在这些战斗中所表现出来的与敌人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无疑是“有确信,不自欺”,“前仆后继的战斗”的具体表现,在民族敌人面前,他们理应和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革命人民同属于民族“脊梁”之列。至于作者在本文中所指斥的失掉自信力而发展自欺力的人,主要指的是国民党政府中的一部分上层人物,但也不宜理解得过于绝对。本文明明写道,这种自欺力已“笼罩了一切”。可见,这种思潮也不仅仅局限于一个阶级、一个集团。恩格斯在论述三十年战争给德国带来的影响时指出,小资产阶级的市侩庸俗习气“已经沾染了德国的一切阶级”,“它既经常笼罩着王位,也经常笼罩着鞋匠的小屋”。“这种旧遗传病毒”甚至“感染”到党内,以至“必须警觉地注意这些人”。联系到作者一贯坚持的对国民“劣根性”的解剖,我们也应该承认,这种缺乏自信力甚至发展着自欺力的现象与人民群众中的某些不觉悟的部分也并非绝缘。正由于此,在困难当头的情况下,强调民族自信力,唤起民族自豪感,就成了思想战线上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而《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就是鲁迅实践这一任务的光辉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