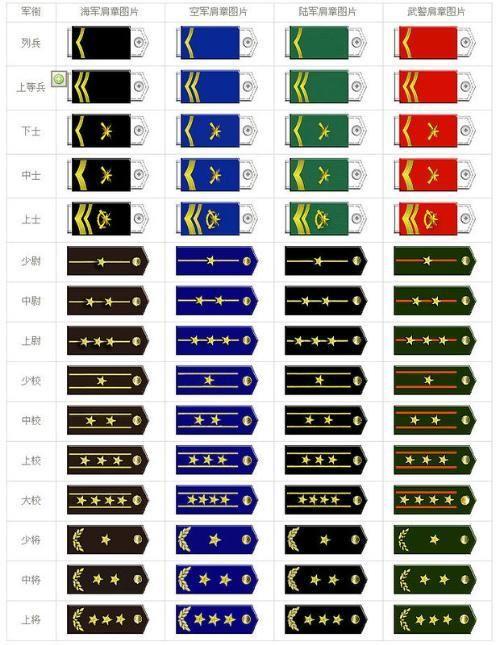中国灵异网的灵异内容
的有关信息介绍如下:道士下山:曝敦煌遗书被发现时的灵异事件
什么叫敦煌遗书?学术界的定义是敦煌出土的公元四至十一世纪古写本及印本,系珍贵的中国古代文献——
发现时间:清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1900年6月22日)
发现地点:敦煌莫高窟
发现者:一位道士,名王圆箓
然而,王道士这次发现,并没有人为之欢呼,也没有人表扬,文化名人余雨先生甚至曾称他是“敦煌石窟的罪人”。未成功臣,反当罪人。为什么?笔者想来原因很多,说到底就一句话:发现的不是时候!
●一个小道士的大发现
人们记得王圆禄,只因他发现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正由于他不经意间的发现,使他一下子成为名人。
历 史定格在1900年6月22日(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甘肃敦煌,一扇历史之门悄悄地被湖北麻城籍道士王圆禄偶然打开,被古人封存了近千年的 5-11世纪的珍贵写本得以重见天日,以至于20世纪的世界文化发现史上注定要记下这样的文字:王圆禄道士发现了敦煌藏经洞。而今密室已不再是密室,渐渐 地人们称它为“藏经洞”,而把藏经洞内的经卷文书称为“敦煌遗书”。敦煌遗书与甲骨文、汉简、故宫明清档案一起,被誉为近代中国四大学术发现之一,并被称 为中国古代文化的百科全书。
遗书发现者道士王圆箓
王 圆禄(1850-1931年)又作圆箓,多被称为“王道士”。湖北麻城人。《麻城县志》载,咸丰六年(1856年)夏天,麻城遭遇旱灾,庄稼几无收成。迫 于生计,王圆箓逃离家乡,来到酒泉一带,入肃州巡防营为兵勇。退伍之后,为解决吃饭问题,王圆箓想出了一个妙法——受戒为道士,道号“法真”。大约在光绪 23年(1897年),他西游来到敦煌莫高窟。其时,莫高窟虽已萧条异常,但因为有百姓的供养,寺院的香火依然时而接续。对已到不惑之年的王圆禄而言,这 个清静的所在正是他度过残生的绝佳选择。
王圆禄发现藏经洞的过程还颇具传奇色彩。开凿于鸣沙山东崖上的莫高窟,由于西北风的长年吹打,流沙 便从窟顶不断地蔓延下来,洞口甬道堆满了沙土,整个洞门都被封了起来。王道士雇了几个伙计帮助清除长年堆积的沙子。那一天,编号为16窟甬道的沙土已经渐 次清理完毕,一位姓杨的伙计发觉甬道北面壁裂一孔,怀疑暗藏石室,于是,王道士与杨某夜半破壁,一个在中国考古学史上难得的惊人发现就这样被一个不知考古 为何物的道士发现了。
洞内重重叠叠堆满了从唐到北宋时期的经卷和文书,王道士面对这么多古代经本和画卷,思考着怎样利用它们来换取一些功德 钱。王道士最先赠送的对象是安肃道台兼兵备使廷栋,不料廷栋这位颇自负的满族官僚只是觉得这些古代写经的书法不如自己写的好,而没有对它们表示特别的兴 趣。但王道士不甘心,仍旧不断地通过各种途径赠送经卷,求得捐助,以至于甘肃的地方官绅有许多人都接受过王道士的经卷赠品。
1902 年3月,湖北人汪宗瀚出任敦煌县令,汪县令很快就得到了王道士送来的经卷和绢画。当这位进士出身、谙熟历史文化的县令见到经卷后,立即判断这些经卷不同一 般,并于1903年冬天,将这一消息写信告诉了兰州的甘肃学政叶昌炽。叶昌炽通过汪宗瀚,不仅获得了敦煌莫高窟留存的碑铭拓片,还收到藏经洞出土的佛画、 经卷和所藏石碑、梵文写本等。只是汪宗瀚所传递的消息极不准确,说洞中经卷只有几百卷,并且好像已经瓜分完毕。所以,叶昌炽虽然一眼看出藏经洞经卷的价 值,但始终没有踏上敦煌一步。倒是那位对王道士态度冷淡的廷栋,后来真的把藏经洞的消息上报了甘肃藩台,但甘肃藩台以敦煌到兰州的运费难以凑齐为由,仅给 汪宗瀚发了一张命令:“就地封存,由王道士看管。”于是,汪宗瀚亲临莫高窟执行这道命令。这是第一次由政府出面对藏经洞进行封存。由于封存措施不力,王道 士表面应承,实际上仍不断地从洞窟取出经卷悄悄出售。直到藏经洞的藏品纷纷被运往国外,造成敦煌遗书的大量外流,当局仍一无所知。
虽然在外国人到达敦煌之前,中国曾有7年的时间可以妥善保护藏经洞写卷,但却一次又一次地失之交臂。接着发生的就是众所周知的西方探险家对敦煌遗书的大肆劫持。尤以英斯坦因和法伯希和为最。
斯 坦因第一次来敦煌是在1907年3月12日。由于不会说汉语,第一次与王圆箓沟通时,王圆禄只答应接受斯坦因的慷慨布施,想看一看书稿,想买几木书卷的请 求被委婉地拒绝了。通过观察,斯坦因发现“王道士尽管对佛教知之甚少,但却对唐僧顶礼膜拜”。于是,在绘满出自当地画匠之手的唐僧传说的道观大殿里,斯坦 因向王圆箓大谈自己对玄奘的崇拜,他甚至以一种近乎迷信的口吻说,正是唐僧的在天之灵将这些密室藏经托付给对佛经一无所知的王圆箓,以等候自己——一个从 印度来的唐僧的崇拜者和忠实信徒即“唐僧之徒”为名,骗取王圆禄的信任。显然,王圆禄被斯坦因“忽悠”了。虽然二人有了共同话题,但王圆禄仍然坚持不让斯 坦因进入藏经洞,而是亲自搬出一捆经卷到大殿的耳房供其翻阅。最终,他接受了斯坦因开出的条件,以40锭马蹄银(合200两银子)的代价出卖了所有被斯坦 因和蒋师爷选中的经卷、帛画,并且追加了60捆汉文写卷和5捆藏文写卷。当斯坦因离开莫高窟时,仅经卷文书装满了24箱子,精美的绢画和刺绣艺术品等文物 又装了5大箱。后经清理,卷文完整的有7000件,残缺的6000件,还有一大批其它文物,开创了敦煌遗书大量流向境外的先例。因为斯坦因不懂中文,他带 走的文件中有很多没有价值的东西。斯坦因第二次来敦煌时,又以500两白银的捐献,从王圆禄手中换去570部汉文写卷。这些卷子是王圆禄专门收集的,均为 完整的长卷,价值极高。
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前脚刚走,法国人保罗.伯希和又来到敦煌。伯希和不仅是汉学方面的专家,而且极富语言天才,至少会讲13种语言。对汉语犹为精通,古汉语中的文言文他都能看懂。
1908 年2月,伯希和到达敦煌。在此伯希和与王道士进行交涉,伯希和流利的汉语很快就博得了王道士的好感,而且,王道士从谈话中得知,伯希和并不知道他把一大批 写本出卖给了斯坦因,所以对这些洋人的坚守诺言感到满意。伯希和同样使用了金钱诱惑的办法,答应给王道士一笔香火钱。经过大约二十多天的交涉,在3月3 日,伯希和就被引进藏经洞,而且还允许他在洞中挑选。
这是外国人继斯坦因之后第二次走进藏经洞,伯希和经过三周调查了藏经洞的文件,最终伯 希和以500两银子(约90英镑),换得了藏经洞6600余卷写本精品和38幅大型绘画。虽然伯希和比斯坦因晚到藏经洞一年,但斯坦因并未能进入藏经洞内 挑选,未能看到全部藏品,而伯希和则不同,他不仅亲自进入洞窟翻检了所有藏品,而且他精通汉语,有着丰富的中国和中亚历史文献的知识,获取遗书的数量虽不 如斯坦因,但几乎全是精品。伯希和后来在一次演讲中称:“在近两万卷子中,只后悔看漏了一个。”
伯希和将获取的卷子从天津以海路运往巴黎 后,于1909年5月来到北京。得知清朝学部筹建京师图书馆,正在“物色各种古籍,以保存国粹”,不知他出于炫耀或别的什么心理,伯希和随身携带一些敦煌 珍本,如《尚书释文》、《沙州图经》、《慧超往五天竺国传》,《敦煌碑赞合集》等在北京六国饭店展示。当时,学部侍郎宝熙、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刘廷琛、京师 大学堂经科监督柯劭忘、翰林院侍读学士恽毓鼎、学部参事江瀚、京师大学堂教习兼学部编译局次长王仁俊、京师大学堂教习蒋斧、国子丞徐坊、知名学者罗振玉、 董康等都前往参观。这些京城的官员和学者看到敦煌写本《老子化胡经》、《尚书》死卷等珍品后,“惊喜欲狂,如在梦寐”,始得知甘肃敦煌有重大发现。
9 月4日,京师学者在六国饭店设宴招待伯希和,出席者有学部侍郎宝熙、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刘廷琛,还有董康、吴寅臣等,其中主要是京师大学堂的一批学者。在招 待会上,恽毓鼎在致词中,正式提出影印其中精要之本的要求,伯希和表示“自可照办”。具体实施者是罗振玉。罗氏又请端方襄助,敦请伯希和出售所携和已运回 国的四部要籍写本照片,伯氏如约,陆续寄到,端方分交罗振玉和刘师培考释。同年中秋节,罗振玉首次造访伯希和于苏州胡同,随即得知敦煌石室尚有卷轴约八千 轴,但以佛经为多。罗振玉立即报告了学部左丞乔茂楠,并由罗代拟电报,命陕甘总督、护理甘肃都督毛庆蕃立即查封敦煌藏经洞,并将所余遗书悉数解运京师。甘 肃方面接到学部电报后,甘肃藩司、代理巡抚何彦升刚刚到任,他命令敦煌知县陈泽藩点查剩余经卷,解运京师。而此时,距藏经洞发现已整整9年。
1910 年,劫余敦煌遗书从敦煌启运。陈泽藩派傅宝书、武相臣两人负责运卷大车的押运。事实证明,傅宝书、武相臣在押解途中,不尽心力,所经之地敦煌卷子任当地官 员抽取挑选,并擅自出卖,又为掩人耳目,一卷撕开充作两卷。之后,才移交学部,共18箱,编号计8679卷。然而,这种分裂经卷以充件数的行径很快就暴露 出来。当时,学部侍郎宝熙发现运送学部的卷子有问题,于是,他写了上告奏折,负责押运的傅宝书被扣留。只因辛亥革命起,清朝官人自顾不暇,不得已,将傅宝 书放回了甘肃,此事也就不了了之。因此,我们在理直气壮地指责外国探险家的时候,我们的内心不免多了一份伤痛和尴尬。
1931年,王圆禄80岁高龄死去。按道家戒律,道士死后不该建塔,但王圆禄的弟子还是为他修建了一座很有气派的土塔,塔碑上记载了他发现藏经洞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