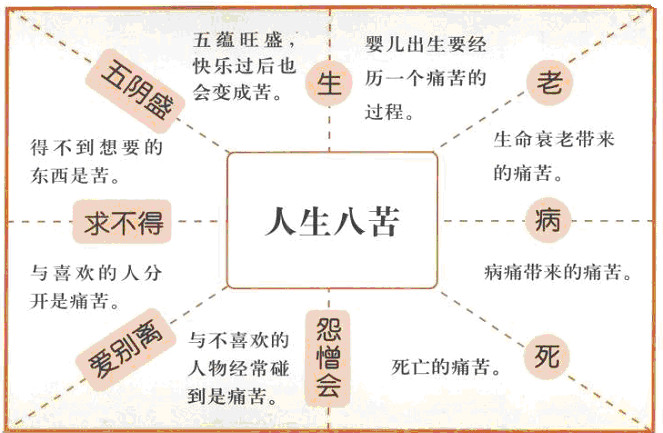何福圣的人生结局
的有关信息介绍如下:
一九四四年九月酒泉解放,当解放大军开进城里时,巳经两鬓花白的熊国炳挤在欢迎的人群里,禁不住热泪盈眶。 后来,人民政府调查流散的红军和苏维埃人员,熊国炳在调查表上填写了自己的真实姓名和过去的职务。但不知是何原因,当时仅把他当作一般流散红军对待,只发给了五十块银元和四石小麦作为一次性补贴。他没有向政府申诉,他巳经习惯了老百姓的生活。后来他被安排到酒泉县人民医院当一个非正式编制的勤杂工。 熊国炳这一次携妻子白玉生回通江老家,他也没有去找当地政府,万里迢迢回来只是尽尽人子之孝。他的父亲巳经过世,母亲和他他大妹住在一起。 我听完后颇替他不平,愤愤道:“现在四方面军虽说被弄得黑不溜秋的,总还有几个人在上面嘛,徐向前、李先念、王树声、周纯全、许世友他们都健在,还有当时在你手下当科长的秦基伟,你为啥不去北京找找他们?” 熊国炳的回答,着实令我震惊!“这事这想过,想开了,也就算了。老弟你想想,当年和我们一起长征的弟兄,死了多少?特别是我作为西路军的一个领导成员,对西路军的全军覆没也有责任,我怎能厚着脸皮去找政府的麻烦?再说,我脱离革命巳经这么多年,岁数大了,身体也不好,去北京找他们,不是让他们为难么?就算得到政府承认,也只是给国家添个包袱,好在全国都巳经解放了,我们入党时的奋斗目标巳经实现了,就是死,也能闭眼睛了。” 我俩从上午一直谈到傍晚,才依依不舍地分手。 自那以后,因我怕连累他,没和他通过一封信。 谁知到了第二年的十月,我突然收到了他儿子从酒泉寄来的信,说他父亲死了,是饿死的。 我难过得很,初时也想到乡场上的邮电所去拍封吊唁的电报,可想想自己头上戴的“黑帽子”,觉得不妥,也就算了。 当夜,我拿上一叠钱纸,独自爬到屋后的山坡上焚烧,向着西北方向久久地敬了一个军礼,为战友送行。我在心里默默地念叼:“永别了,大舅倌!永别了,巴山英雄!”